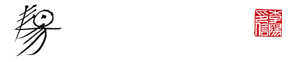【彩排】——关于李阳的画(张渝)
彩 排
——关于李阳的画
张 渝
张渝(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)

笔名雪尘,祖籍辽宁,1964年生于重庆,现居西安。1989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,现任陕西省国画院研究员、陕西美术博物学术委员。已出版专著《雪尘语画》、《青春的子弹》、《书法主义》,在全国美术及书法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二百余篇。写作之外特爱飚车,曾创造从西安到洛阳二小时四十分钟的个人纪录。
不施粉墨的李阳想不到彩排,也想不到我会用“彩排”两个字来谈论他的画。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,是因为李阳目前的创作在我看来就是一场彩排。这样的结论与他在国内画坛的名气以及他美院教授的身份没有关系,与之关联的只是其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。当所有的经验集结在号称天域的藏地时,李阳所做的事一定不会小。于是,有了彩排。当然,他的彩排不是为了表演,而是为了净化;不是为了破解藏地密码,而是为了寻找心灵净土。
李阳的彩排首先来自于色彩。无论西藏唐卡,还是敦煌壁画,李阳都做了深入研究。他从日本岩彩入手,在厚与重的审美维度上,展示虔敬而非秘密或神秘的模样。自然,我们很容易在李阳的色彩中感受到神秘的氛围,比如我非常看好的《华山雪》。如果不是高海拔藏地所提供的艺术经验,李阳笔下的“华山雪”不会是我们今日看到的模样。自明代王履的《华山图册》之后,“华山”成了众多画家的一个题目。在这个题目下,画家们的精力大多放在了华山的险与雄上面,他们努力的也只是“无限风光在险峰”。然而,众人目中的险与雄在我看来却更多形而下的因素,真正形而上的还是藏在险与雄之后的神秘及神圣。而艺术的风骨往往就在那里。离开了神秘或说神圣,我们往往站在了形而下的层面。而形而下的层面所能有的只是风光而非风骨。
较之风骨的审美高度,风光显然是形而下的。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,我特别看重李阳笔下的《华山雪》。在中国绘画史有关“华山”的图形谱系中,李阳的“华山”有了新的形态与样式,而这就是创新。
说到创新,我必须指出的是:当我说李阳借助有关藏地艺术经验创造了有关华山的新样式时,并不是说他笔下的“华山”就超越了张大千、石鲁、何海霞、罗铭等人笔下的“华山”,而是说他创造了新的有关华山的艺术想象。在他的想象中,我们又多了与“华山”联系的方式。批评家王彬彬曾借助毕加索谈过创新。他说,在文学艺术中,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所谓进步,创新只是创造了一种新的与现实联系的方式,而古典大师创造的方式作为与现实联系的可能方式中的一种,永远有着不可磨灭,不可取代的价值。李阳有关“华山”的创新恰可如是观。
在赞扬了李阳的“华山”后,我再回到他的《华山雪》。上文说,这是我看重的作品。但现在我要说出自己的遗憾。这遗憾便是他对作品的命名。在我看来,《华山雪》中的那个“雪”字实在是狗尾续貂。因为真正使其作品奇特的不是华山的“雪”,而是“华山”。不是“华山”风光,而是“华山”风骨。当然,就就李阳的整体创作看,如此续貂之笔只是他艺术彩排的一个插曲或花絮。因了这类花絮的存在,李阳的“彩排”有了意义。
除却“华山”,李阳几乎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藏文化或说佛文化圈。在这个圈里,作为题材的西藏与印度、尼泊尔的区别只有形而下的区别;在形而上层面,三者具备高度的一致性。
我不想从宗教或仪式的层面来谈论李阳的创作。尽管这在画面上是显而易见的。我想谈论的只是他的敏感。
李阳的艺术营养非常庞杂,古今,中外都有。但统摄这一切的还是敏感。生性敏感的心灵容易受到伤害,也容易受到感动。我相信李阳的创作来自他的感动。他的作品多以大山大野为依托,然后以逆光的形式塑造人物。在人物塑造上,他强调的不是形象,而在态度。也就是说,他关注的是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态度。
众所周知,藏区或说高原的天总是最蓝的。但李阳取了灰调。他这样做并非是刻意营造神秘,而是他敏感的心灵感受到了神秘。他笔下的人物绝少正面造像,而且大多只是低头的轮廓。不过李阳抓住了这一低头的瞬间。其实,除了李阳,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人抓住了这“一低头的瞬间”。那人就是徐志摩。在名作《沙扬娜拉——致日本女郎》中,徐志摩甜密而又忧伤地写道:
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,
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,
道一声珍金,道一声珍重,
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——
沙扬娜拉!
如果说徐志摩展现的是密甜的忧愁,那么,李阳强调的却是因虔敬而来的敬畏。他强调的不是宗教仪式,而是人生态度。由于如此强调,李阳的创作又一次具备了彩排的意义。他的意义在于参悟佛心,而不是佛身或者西藏风情成了主题的当下时潮。
在李阳之前,艺术家们于佛之一道并不陌生,以禅佛入画而别开艺术格局者也大有人在。但李阳以自己的敏感抓住了姿态,在瞬间的姿态里,李阳讲求的不是佛之“了生脱死”,而是菩萨级的“留惑润生”。因为佛学中说,佛是觉者,可以了生脱死。而菩萨故意不断生死,留一点来帮忙世人,来广度众生,也就是前文所说的“留惑润生”。
在一低头的瞬间的惑中,李阳以及他笔下的人物有了来自佛光的滋润。绘画史上,有关西藏、宗教、风情的艺术谱系也因之有了新的创作路经。我实在不愿意用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这句已经俗滥的话来比附李阳的创作路经,但又实在没有更好或者更恰当的言辞来比附。因为李阳的创新之中,还太多符号性的东西,他似乎生怕我们忘了他的艺术与西藏与佛的关联并时时提示我们。也正是基于此,我说李阳的创作是一次隆重的彩排,它不是为了表演,而是为了修正。它关注当下,却更加瞩目未来。人说,一直在直播的人生没有彩排,然而,天地一梨园,人生天地间,如生如净如旦如末如丑。面对此等角色,怎么可能没有彩排?基于此,“彩排”的李阳有了自己的意义。
- 上一篇:【有一种悠远闪着灵性】李阳人物绘画释读(西沐) 2014/3/21
- 下一篇:没有啦